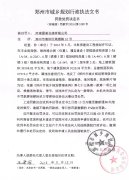文 / 楊大俠 1991年,梁穩根打算更換企業的名字。他想起失敗的過往:販羊、賣酒、做玻璃纖維。這些經驗,成為了他創業的初衷:創建一流企業,造就一流人才,做出一流貢獻。這是“三一重工”的發軔緣起。 2011年,三一重工成為國內工程機械第一品牌,它以215.84億美元的市值登上《金融時報》全球500強,梁穩根也以500億身家,從曾經的販羊少年,成為內地首富。
梁穩根 而在今年12月14號,三一宣布:擬以40.77億元的價格轉讓全資子公司北京三一重機100%股權。在此之前,北京三一重機就已進行過一次瘦身和應收賬款的轉讓。此次,它實在無法稀釋壞賬。 從篳路藍縷的起步,到笑傲群倫的鼎盛,三一走了22年(1989年到1991年,三一叫做湖南省漣源市焊接材料廠);而繁華的凋零,不過短短5年光陰。三一的走衰,是整個中國工程機械行業的走衰,它們都在大環境的蕭索、傳統制造的沒落、互聯網的沖擊之下,尋找重生的血脈。 崛起:左手技術,右手資金 有人評價希特勒的一生所為,用了八個字:左手利刃,右手真理。如果對三一重工進行一個類似的歸納,那就是左手技術,右手資金。 這兩只“手”,也是扼制三一在早幾年發展的鐵鉗。80年代末,是改革覺醒、經濟復蘇的過渡,它解放了勞動力,也解放了人們的思想。城市工業文明的星火開始點燃全國各個角落,也點燃了梁穩根和他幾個大學同學的熱情。他們喝酒立狀、滴血盟誓:為民族工業的振興而奮斗!
年輕的梁穩根和他創業伙伴 但盟約只能是盟約,無論多堅定,它始終無法變成實質的利益。1993年,在嘗到做基建重工的甜頭后,梁穩根把公司扎根到了長沙,描摹他更大的宏圖——做高利潤的混凝土拖泵——這在當時,只有工業國企敢做。慘淡的銷量讓他終于明白:振興民族不是靠一腔熱血,而需要實實在在的高新技術,引入技術的代價,就是價值對等的資金輸出。 此后,三一視技術為第一生產力,梁穩根不斷從北京、廣州等發達城市和國外學習新技術,企業同時不斷高價挖來技術工程師。兩年時間,三一混泥土泵不僅突破技術壁壘,還一躍成為中國市場份額第一。 隨著工程機械市場多樣化、復雜化的推演升級,三一也不斷向業務邊界進行開辟拓張,相繼研制出全液壓壓路機、全液壓推土機等有市場競爭力的重工產品。2003年,三一上市,獲A輪9億融資,此時他們擁有的不再只是同質化產品,更多的是專利技術的獨家產品,當中的輸送泵突破了三級配混泥土不能泵送的難題。2009年,三一混泥土機械的營收擊敗了普茨邁斯特,成為全球第一。 接下來的3年,是新千年里工程機械的第一個春天。國家頒布的“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”,催生了龐大的基建項目,這使整個行業欣欣向榮的同時,也讓三一走向“人生巔峰”。2012年,三一收購了全球混泥土機械第一品牌普茨邁斯特90%的股權,近乎壟斷了國內工程機械市場,成為絕對的鰲頭。 縱觀三一整個崛起發展史,可以發現其成功的兩大因素: 一是公司從漣源遷到長沙。漣源在1987年才由縣轉為縣級市,其資源環境、市場、資本等均不成熟,其所屬的婁底市,更是處于經濟墊底的位置;作為省會的長沙,在各個方面對比于漣源,無疑都是霄壤之別。
三一在漣源 二是技術與資金的雙管齊下。互聯網狂潮洶涌而至的前夕,傳統工業是一個很單純的領域。這個領域中,用技術做好產品、賣取利益,同時用資金學習新知、挖取人才,研發更先進的技術,做出人無我有的產品,立于不敗之地也就順理成章。 低迷:政策轉向,積重難返 然而,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:除了星辰日月,沒有什么是永恒的,帝國如此,企業也如此,就算你把控住內部的一切,你也無法違逆上天的安排。三一的悲情之處在于,它遭受了大環境的“迫害”,內部管理也逐漸失控。 2011年,在品嘗到50%盈利暴增的利好后,三一如同脫韁野馬,膨脹的野心與瘋狂的舉動再難收勢。而此時,老天似乎給它開了個玩笑。 2012年,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重點轉為“穩增長”,對成熟產業的國有固定投資有所下降,轉將更多的財力投入到基礎設施和新興產業里。從現在往回看,不難得出,所謂的“新興產業”,就是如今人人稱頌的互聯網。 國家的投資,影響到企業的投資,投資人愿意花更多的錢投入互聯網和金融行業,因為這類行業投入小、回錢周期快,他們早已厭倦把錢投入到幾年都不冒一個泡的傳統工業。 此外,國家對環境、山體、礦產資源的保護、對煤炭行業的遏制與日俱增,致使煤廠、建筑行業對基建機械重工的需求也日益減少,而這,無異是三一盈利最重要的渠道。 遭受外圍環境重創的同時,三一內部也在止不住的膨脹中加速內耗。先是企業員工隨盈利的陡升而暴增。數據顯示,2009年底,三一總體員工21598人;截止2010年底,員工增加到42367人。一年時間,員工增幅高達96%。無疑,這多出來的2萬多人,都成了大環境下的犧牲品。 其次,三一在連續幾年排行產業龍頭老大之后,極力擴大了產能,并采取激進的營銷策略:層層分銷。這就導致工程款一環扣一環,難以及時收賬。據統計,三一在2010年到2011年里,應收賬款達到了113億。這對于三一1000多億人民幣的市值與當年507.76億的營收來說,或許不算什么,但對于接下來的行業走衰,它就是救命稻草。
三一近6年的應收賬款持續走高,且與計提懸殊越來越大 再次,當國家經濟策略發生改變時,三一的主戰場還停留在國內。據三一現任總裁向文波表示,在2008年之前,三一的海外銷售額,不足10%。2012年,三一收購普茨邁斯特,應是三一表示出海的決心,但也就在這個時候,行業萎縮了。 大環境政策的轉向,企業曠日持久堆疊的積重難返,最終不得不以瘦身的方式來維持內部供血,三一重工的問題是:無論在什么時候、什么階位,都別忘了給自己留一條后路;在激進地跑馬圈地的時候,也別忘了“振興民族工業”的初心。 破冰:尋找續命血脈 自2011年以后,三一的盈利持續下滑:2012年,三一盈利下滑7.76%,全球排名下降到第4。截止去年底,其盈利不足2011年的50%;今年,三一排到了第12名。
三一5年盈利表 三一重工困局的背后,是整個工程機械的寒冬。據中國工程機械工業協會數據,2012年前七個月,工程機械行業利潤總額同比下降20.3%;廣發證券在2014年統計了包括三一、徐工、中聯、柳工在內的9家工程機械上市企業,其合計營收下降為高峰期的50%左右,凈利潤則只能達到高峰期的20%。 群體性的頹勢引發了各自的反思,總結其共性,大致有以下幾點:一是政策走向,這無法抗衡;二是互聯網的沖擊,讓資本的天平發生傾斜;三是共享經濟的崛起,讓人們的消費行為從購買變成租賃;四是流水化的作業,讓生產更為便捷,導致產能過剩。 對此,各大重工企業紛紛踏上尋找續命膏血的探索逆旅: 三一重工借力“一帶一路”,依托大企業開辟海外市場,同時進行海外并購、投資等舉動;同時,在海外建立研發制造基地和銷售公司,形成全球化格局。這一舉措,讓三一在2015年的海外業績提升到44%。 徐工機械進軍高端裝備與智能化市場項目、環保項目等,同時依托互聯網,進行產業轉型升級,以及開拓海外市場。這一決定讓公司第三季度營業收入實現11.14%的同期增長,凈利潤更是實現319.34%的同比飛躍。 受分享經濟影響,中聯重科與一家二手機械電商平臺達成合作,跟隨“新常態”步入工程機械深度調整期,降低運營成本的同時,高效去庫存。據統計,國內二手工程機械保有量已高達700萬臺,這是個很大的市場。 通過這些舉措,我們也可大致窺探出工程機械逃離寒冬的方法: 首先,工程機械產業的定位必須發生轉變。現在的工業,不再是從前單純的朝陽產業,服務業已經后來居上。供給側改革的政策轉向,也將服務業轉變為經濟增長的主引擎。從這一點反觀三一,如果它在2011年收住腳步,配合“穩增長”,或許它的結果,不至于讓內部分崩離析。 其次,與互聯網接軌。當需求方消費乏力,不妨把目光投向海外消費者;當企業庫存過多,不妨賣更便宜的二手機械,抑或將庫存出租而不售賣。前者連接海外市場,后者接軌分享經濟,這都是互聯網的作用與優勢。如果夠幸運,引入投融資也并非不可能。 再次,實現傳統機械到智能化的產業升級。順應環保最大的工業啟示,就是電動車的出現,這也是給予工程機械行業的啟示。如果工程機械實現電動化,或許它還能帶動該產業的消費升級。 最后,是國家的態度。國家對工業投入的邊緣化與空心化,引發了政協委員李毅中的不滿:“放松對中國工業重視和投入,就脫離了中國國情”。誠然,同為三大產業,如果根據眼前利益而按比分配、厚此薄彼進行投入,中國經濟的穩步發展也無從談起。 更多精彩內容,請點擊http://t.kanshangjie.com/r4
三一的瘦身,是一場內部的震蕩,也是工程機械行業面臨的問題。它不足以引起該行業的軒然大波,也不會改變整個產業的走向,但至少,作為一個借鑒,它會引發我們對重工產業、乃至整個工業寒冬的思考。 |
曾經市值千億,如今41億瘦身:三一的興衰與困局
時間:2016-12-20 16:32
來源:商界作者:商界
中國傳媒聯盟 據 商界 訊:三一的走衰,是整個中國工程機械行業的走衰,它們都在大環境的蕭索、傳統制造的沒落、互聯網的沖擊之下,尋找重生的血脈。
頂一下
(0)
0%
踩一下
(0)
0%
------分隔線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